
任何试图拒绝道德、义务等规范概念的哲学根本不可能阐明“德性”,而缺失“德性论”的伦理学根本就不是“实践”伦理学,伦理学的实践必定是指向人自身“成人”,即伦理理念和道德原则内化为自身的德性品质。把两者对立起来、分割开来的伦理学显然是作茧自缚,不可能成功,因而也是没有前途的事业。美德伦理学要能在现代取得成功,真正能够成为能与义务论和后果论相提并论的伦理学体系,必须继续在实践哲学的基础理论,即实践的形而上学(伦理形而上学)上能够取得突破,并在美德伦理的相关领域进行延伸性的探究。
——邓安庆:《美德伦理学:历史及其问题》(《伦理学术7——美德伦理新探》之“主编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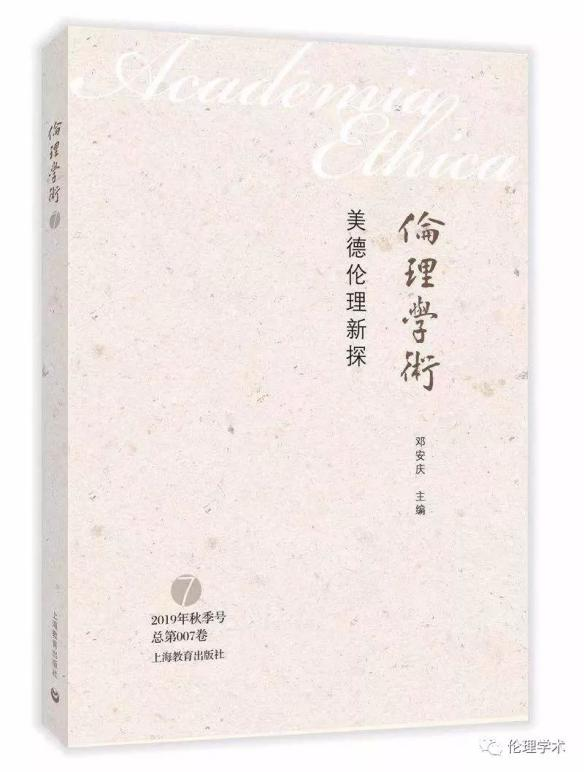
《伦理学术7——美德伦理新探》
2019年秋季号总第007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19年12月
目录
【主编导读】
美德伦理学:历史及其问题
邓安庆
【原典首发】
海德格尔、《黑色笔记本》与灭绝犹太民族
「法」埃曼纽尔·法耶
刘剑涛 张晨/译
【原著导读】
性差异:一种激情伦理学
张念
【美德伦理学】
伦理视野下的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
王晨
自然、理性与德性
——斯多亚学派的德性理论
叶方兴
沙夫茨伯里的美德观念:以伦理学演化史为视角
陈晓曦
休谟伦理学的美德伦理之思
赵永刚
马克思与革命的美德
「美」弗雷德里克·G·韦兰
王贵贤/译
【美德政治学】
美德政治学:对现代自由主义的一种反思
陶涛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论有美德的生活与政治
张容南
论贤者宜负重责
——缓解美德政治对政治美德的压制
贾沛韬
语言的暴力与解放:从动物伦理到生命政治(上)
李金恒
【美德法理学】
美德法理学:以美德为中心的裁判理论
「美」劳伦斯·索伦
胡烯/译 王凌皞/校
美德理论与至善主义法学:价值与限度
「美」罗伯特·乔治
孙海波/译
【美德认识论】
智德与道德:德性知识论的当代发展
米建国
作为能力知识的“理解”:从德性知识论的视角看
徐竹
理智德性:值得钦慕的品质特征
「美」琳达·扎格泽博斯基
方环非/译
【描述伦理学】
难道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接受惩罚吗?
——评电影《何以为家》
余达淮
【让哲学说汉语】
泰西哲人杂咏(三)
钟锦
【书评】
改变需要抑或是改变世界
——读努斯鲍姆《欲望的治疗》
叶晓璐
美德伦理学:历史及其问题
邓安庆/文

“主编导读”作者:邓安庆 教授
一、美德概念之本源和美德伦理学之兴起
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如果就Virtue的希腊词源而言,翻译为“德性伦理学”更为准确,因为在被视为Virtue Ethics最为经典表达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德性”是个中性词,他不仅研究“美德”,而且也研究“恶德”,甚至不在我们当今的“伦理”或“道德”意义上使用,而是在“物性之功能”、特长上使用:人有人的德性,马有马的德性,刀有刀的德性,胃有胃的德性,说的都不是道德上的“美德”,而是功能上的品质。“德性”是万事万物“自然获得”的基本品性,“天然的品质”,每一“事物”都有一种内在的、将其自身偶然获得的“天然品性”自我造化出“最优”“最好”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它的“德性”。如“眼睛有眼睛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说的就是“眼睛”具有把它自身的基本功能“看”的“品性”发展到最优状态的能力。当我们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说“胃有胃的德性”时,也是就“胃”自然获得的品质:作为一个器官的“消化功能”而言的,就是说,“胃”把它的消化功能完全实现出来,实现到“最优”,它是一个“好胃”,一个“有德性的”“胃”。所以,古希腊人讲“德性”时,他们说的是:ἀρετη'/arête,一方面是事物天然具有的品性,一方面是这种天然品性(作为某种“功能”)自身具有的“最优化”能力。前者是“潜能”,后者是“实现”,德性是促使“物性”由“潜能”到“实现”的能力。把这样的“德性”词语翻译为我们现代的“美德”,显然不是含义对等的表达,因为它更多的是用于非人类行为意义上的每一个事物、每一个器官及其部分的“功能实现”所体现出来的事物本身的某种特质、特长或功能,而非特指人类的人格品质和行为品质。因此,港台学者通行将其翻译为“德行伦理”,也同样是与古希腊的含义不甚符合的。
当然,Virtue不是希腊语而是拉丁语的写法,它的含义有些许改变。virtue来自拉丁语virtus,词根vir即男人,其形容词形式virile,即是“男性的”,有男子汉气概的意思。古罗马神话中有一个广受崇拜的神只Virtus(维尔图斯)是刚毅、勇猛的铁汉形象,这个形象塑造了古罗马文明的鲜明品质。虽然勇气、勇敢在古希腊也是最为重要的德目之一,但并没有直接以它作为美德的词根。“美德”是把Virtue道德化,更强调“德性”/“德行”是“人为”的善举,是在人类生活中正确、公正和智慧的恰当表现,而ἀρετη'/arête不限于人,本义是一般“物性”“自然的”“本质的”力量表现。所以,如果是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使用Virtue Ethics,“德性伦理学”还是其最理想的表达。
本文的标题之所以用“美德伦理学”,是因为当代英美的哲学家试图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伦理学类型使用它,因此,把它当作一个区别于古代“德性论”的新概念,翻译为“美德伦理学”也是一个好的选择。虽然当代美德伦理学家一般都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作为典范,但古代却没有出现一个“美德伦理学”概念来标识自己的伦理哲学思想,我们一般也都是把“美德伦理学”视为一个地道的当代英美哲学概念。这样说来,这个概念就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即从1958年牛津大学哲学家伊丽莎白·安斯库姆(G.E.M. Anscombe,1919—2001)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杂志上发表《现代道德哲学》一文,才是它的开端,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引起广泛共鸣的复兴传统德性伦理的潮流,力图把这种“美德伦理学”与现代两种主流的规范伦理学:康德“道义论的义务伦理学”和英美“功利论的后果主义伦理学”并列,作为规范伦理学的一个不同类别。从这时起,学界才流行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称之为“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而亚里士多德自己只把他的伦理学当作从属于“政治学”的“实践哲学”。

伊丽莎白·安斯库姆(G.E.M. Anscombe)漫画像
安斯库姆的《现代道德哲学》之所以能起到一面旗帜的作用,实际上是与该文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清算与批判契合了人们对于现代伦理学的不满情绪有关。该文对功利主义道德哲学的批判,应该说是切中要害的:“后果主义是他以及自他以来的每一个英语世界的学院派道德哲学家的标志性特征。通过它,以前会被视为一种诱惑的那种考虑,那种由老婆和阿谀奉迎的友人向男人们力陈的考虑,由道德哲学家们在他们的理论中给予了一定的地位......后果主义是一种浅薄的哲学,这是它的一个必然特征。”而对康德义务论伦理学的批评则给人不着边际之感:“康德引入了‘为自己立法’的理念,这与如下一种情况一样荒唐,即在一个多数票要求极大尊重的现时代,人们要把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个反思决定都称为导致了多数票的一票......没有关于何者可以算作对一个行为的贴切描述——这种描述带有一种构造该行为的法则的观点——的约束条件,他关于可普遍化法则就是无用的。”但对现代道德哲学的这种整体批判显露出作者一个非常敏锐的洞见,即她认为,自西季威克以后,英语世界的道德哲学界有名气的作家们之间的区别微不足道,他们都在一种越来越狭窄的伦理学视野下从事道德规范的合理性论证,而并没有为道德规范的有效性提供如同亚里士多德德性论那样的一种关于一个人的完整美德的规范:“这个具有一整套美德的‘人’就是那种‘规范’。一如具有一组牙齿的‘人’是一种规范一样。但在这个意义上,‘规范’不再与‘法则’大体等价了。在这种意义上,关于一种‘规范’的观念让我们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伦理学较之以与一种伦理的法律观念更接近了。”
但把一个“有美德的人”本身作为“规范”,以反对现代的“规范”伦理,实质上是把“美德”与“规范”对立起来了。表面上看,这是以“内在的美德”去反对“外在的规范”,但实质上当我们把那个“有美德的人”作为“我的”规范时,那个“人”对“我”而言,恰恰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例如,当我们把“雷锋”作为我们的道德楷模时,我们是要去学习他做“好人好事”的“原则”,是这个“做人的善的原则”让“雷锋”成为“雷锋”的美德(做好人好事),而不是简单地去学习他所做的“好人好事”。如果是后者,那我们就只是把雷锋这个人作为我们“规范”的基础,“雷锋”就没有内化为我们内在美德的“原则”。相反,康德强调伦理的和道德的规范,区别于法律的规范,恰恰是内在的,当把合法的法律规范,自愿地转化为我们的“动机”,规范、义务才是“伦理的”。安斯库姆在把“规范”和“美德”对立起来的同时,认为从事道德哲学只要我们拥有一种令人满意的心理哲学,证明一种义务或责任在心理意义上是可能的,道德义务和责任以及对“应当”的道德意识的概念,统统“都应该被抛弃”,真是过于大胆和极端的言辞。
整个说来,实际上安斯库姆这篇文章的意义,不在于她比现代道德哲学提供了什么更好的论证,而在于她为复兴传统德性论伦理学指出了方向,但她把“规范”与“美德”对立起来,只谋求对德性做出某种心理说明的倾向,乃是与从康德到胡塞尔以来致力于建立一种严格科学的哲学要求背道而驰,也预示了之后的美德伦理学最多只能在道德心理学上有所建树,而很难在哲学的基础论证上超越传统伦理学,甚至有可能还根本不如现代道德哲学本身,它的意义更多地可能只限于一种“复兴”的号召。因为专注于从心理哲学去论证,把“美德”理解为单纯的心理倾向或秉性,是非常容易的,甚至把美德的基础理解为心理上的同情或移情,但这种纯粹心理主义的阐释都跟真正的“道德感”无关,不用说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情感主义,康德的道德情感理论都已经超越了这一阶段,甚至连随她之后发展美德伦理学的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1929—)都不会同意这样做。决定于个体美德的,虽然有心理机制的自然作用,但人的社会性或政治性使得心理潜能无不在坚硬的社会政治现实实现面前遭遇被塑造和改变的命运,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美德伦理学的后起之秀讨论道德运气了。单纯的心理机制必须在社会文化精神共同体的互动中才能完善,这也就是麦金泰尔试图从社会共同体、社会目的论去改造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的理由。如果仅仅依赖于一种心理哲学来论证伦理的规范或美德,都是不可能成功的,或者说它根本不是阐明伦理或道德的美德之唯一合适的基础。

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
二、美德伦理学的类型
在安斯库姆之后,关于美德伦理学的讨论越来越多,他们一个总体倾向就是,试图把美德伦理学论证为与道义论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并列且比它们更有优势的独立类型的伦理学类型。福特(Philippa Foot,1920—2010)曾这样描述“美德伦理学”起初的发展:“许多年来关于美德与恶习的主题被分析传统的道德哲学家们忽略了。 对此缄默不语起因于人们认为,这不属于道德的基础,而且由于像休谟、康德、密尔、摩尔(G.E. Moore)、罗斯(W.D. Ross)和普里查德(H.A. Prichard)这些当今道德哲学的绝大部分都是由他们所主导的哲学家们,表面上也有这种看法,这种忽略也许根本就不值得惊讶。 最近时间内事情似乎也发生了变化。 在前十至五年时间中,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才转向这一主题,尤其是冯·莱特(G.H. von Wright)和彼得·吉奇(Peter Geach)。 冯·莱特于1963年出版他的书《多种多样的善》(The Varienties of Goods),为诸美德的贡献确实不是表面上的一章。 而彼得·吉奇的书标以《论美德》(The Virtues)之题于1977年面世。 从此之后,为此主题出版了一系列令人感兴趣的杂志论文。”

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
这也就是说,美德伦理学起初的发展是对分析传统的道德哲学忽略美德现象开始的,而这种批判随之从分析哲学转向了对整个现代规范伦理学的批判,促使大量重视美德的文章出现,一直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基本上处在这种状态中。1978年,詹姆士·华莱士(James D. Wallace)也还是像这些学者们一样出版了《诸美德与诸恶德》(Virtues and Vices),但到80年代,随着麦金泰尔一些具有创造性的论文和著作的出版,带来了一个新局面:“真正将美德的重要性同伦理学的探究模式相结合,并带入更广泛讨论中来的,仍要归功于麦金泰尔在20世纪80年代的杰出工作。”麦金泰尔1984年出版的《追寻美德》(After Virtue)已经成为美德伦理学的经典著作,他还出版了许多有关美德伦理学的其他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伦理学简史》等。 麦金泰尔不仅是在批判现代规范伦理学不足的意义上,而且更在美德伦理学本身的形态上讨论美德伦理。 他特别突出地强调了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确立的理论框架“目的论”:伦理学是为了实现人类所有活动的最终目的——幸福——而必须培育自身的美德,美德是实现人生幸福的美好品质。 他也看出了这种美德伦理实际上需要依存于城邦政治的伦理实体:以社会共同体的传统与实践所认同的共同善来塑造。 因此,麦金泰尔美德伦理的构想,一方面有亚里士多德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联系,大大超越了其他英美美德论者。 在麦金泰尔之后,美德伦理学发展起来而且显然朝向了几个不同方向上发展。 根据高国希和叶方兴的研究,他们把美德伦理区分为如下四种类型:新亚里士多德主义(Neo⁃Aristotelian)的美德伦理学:新斯多亚主义(Neo⁃Stoics)美德伦理学: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或新休谟主义(Neo⁃Humean)美德伦理学和德性自我主义或尼采主义美德伦理学。
当代美德伦理的基本类型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麦金泰尔、福特和赫斯特豪斯(Mary Rosalind Hursthouse,1943—)。 福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道德哲学,但涉猎广泛,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应用伦理学都有她的贡献。 著名的“电车困境”就是由她最先提出来的。 在美德伦理学领域,她被称为除安斯库姆、麦金泰尔之外的第三位奠基者。 她与安斯库姆一样,以“美德伦理”反对“现代规范伦理”,但与麦金泰尔不一样,她始终坚持自然主义的美德立场,这也就更加接近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立场。 在美德上,她除了弘扬传统的四主德:勇敢、节制、智慧和正义外,特别重视仁慈、博爱的价值,这也就在价值观上不仅复兴古希腊的古典价值,而且延伸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核心价值。 在道德判断问题上,她赞同我们从后果考虑行动的道德性,认为道德判断具有预设的特征,其规范的效力取决于与行动者有相适应的利益和愿望。 她的主要著作有:《美德与恶德以及其他道德哲学论文》(Virtues and Vices and Other Essays in Moral Philoso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Oxford:Blackwell,1978):《自然的善》(Natural Goodness. Oxford:Clarendon Press,2001(此书被翻译为德文:Suhrkamp Frankfurtam Main 2004),《道德困境以及道德哲学其他主题》(Moral Dilemmas. And Other Topics in Moral Philosophy,Oxford:Clarendon Press,2002)。

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
赫斯特豪斯是复兴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的重要旗手。 她的代表作《美德伦理学》(On Virtue Eth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一开篇就力陈“美德伦理学”是个“专有名词”,标识那种强调美德品质而非义务或规则的伦理学思路。 她要“详加讨论的这种独特的美德伦理学版本,是一种比较普通的类型,名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 该普通类型之所以‘新’,至少是因为我前面提到的那个理由,即,支持者俨然允许自己把亚里士多德视为明显错误的,同时,我们没有让自己的看法局限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清单的范围。 (比如,仁慈或慈善就不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但所有的美德伦理学者现在都把它列入清单。)而之所以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则是因为无论什么地方,它都以牢记坚持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著作为宗旨。 因此,我这里提出的仅仅是美德伦理学诸多可能样式中的一个版本。”
这显示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学”决不意味着只是单方面地“复兴”或“弘扬”经典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思想,而是既有继承,同时也蕴含着批判。 当然与他们的宗旨相应,在这一支脉的发展进程中更多的是涌现出了许多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坚定捍卫者。 如年轻的温特(Michael Winter,1965—)于2012年出版《重思德性伦理学》,驳斥人们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种种批评,试图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语境捍卫他的德性论,认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最大优点就是面对、处理复杂的社会情境具备灵活性(flexibility)。 但大多数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采取的是赫斯特豪斯那样的态度,更多的是在当代伦理生活处境下依据亚里士多德,补充亚里士多德的论证,剔除他的不可接受的错误观点,而对他的依然具有意义的德性论“运用于”解决当代人的伦理难题。 如赫斯特豪斯在《美德理论与堕胎》(Virtue Theory and Abortion)中,就“应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美德理论来解决当代人的堕胎困境。 她的努力显示出她试图打破一直以来理论/应用、事实/价值之间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亚里士多德实践—本体论中根本就不存在。
新斯多亚主义的美德伦理学,是除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之外的另一支重要力量,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1947—)她的成名作《善的脆弱性: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早已在国内拥有大量读者了。 在该书中她借用诗人品达的葡萄藤之喻,这样来阐明了一种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的美德观:“人的卓越就像葡萄藤那样成长,得到了绿色雨露的滋养,在聪慧而公正的人当中茁壮成长,直达那清澈的蓝天。”但“阳光雨露”,“根壮土沃”,可遇不可求,一个杰出的人虽然有责任培育自身的卓越,但时时刻刻需要“有运气”获得外界的滋养,否则,孤立无助或无常的变故也会随时摧毁世上任何一个本来就细弱的生命。 因此,人生的繁荣发达,单靠人的理性是不自足的,哪怕具有坚定地追求正义美德的个人,也容易受到外部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随时可能严重威胁着个人的成长,使得人不得不带有各种不稳定的情绪面临捉摸不定的“道德运气”。 人类能够抵御危险、赢得运气的东西只有他的善良,而承认人的脆弱性将是人类具备善良的关键。 所以在伦理学上,努斯鲍姆选择了回避柏拉图,而倾情于古希腊悲剧剧作家和亚里士多德。 她提倡一种关注人类普遍关怀并实现幸福生活的美德理论。 但她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致力于思考如何选择优良政体以实现城邦政治的善治,在参与政治生活中实现人的政治本性,并进而实现自身的美德,借助于美德实现作为最高善的幸福。 她之所以被称之为新斯多亚主义美德伦理的代表,更主要的是因为她的幸福观和美德论,更类似于斯多亚主义,或者说她的思想资源更多的是斯多亚主义的。 这尤其从努斯鲍姆的哲学研究特别注重情感领域找到更多的理由。 她对情感的描述和辩护,具有明显的斯多亚主义风格,特别强调对情感的自我控制,情感分析对于心灵治疗的哲学意义。 同时她对悲伤、同情、爱、厌恶和羞耻等广泛的情感现象作出了有价值的分析。 这些分析可以印证一个斯多亚主义的美德观:成就自身的德性即幸福。 在努斯鲍姆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The The rapy of Desire: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llenistic Ethics),她的新斯多亚主义倾向更加清晰。 虽然这并非专门讨论斯多亚主义情绪控制与心灵治疗的书,而是涉及了对整个希腊化时期哲学的讨论,包括伊壁鸠鲁主义、怀疑主义、犬儒主义等。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情感主义美德论或新休谟主义是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另一种类型。 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迈阿密大学哲学系的斯洛特(Michael Slote),他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教授,出版了大量美德伦理学的著作:《善与美德》(Goods and Virtue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3),《共通感:道德与后果主义》(Common⁃Sense Morality and Consequentialism,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5),《从道德到美德》(From Morality to Virtu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攀越最优化:合理选择研究》(Beyond Optimizing:A Study of Rational Cho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出于动机的道德》(Morals From Motiv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关怀与同情的伦理》(The Ethics of Careand Empathy, Routledge,2007):《伦理学史散论》(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Eth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道德情感主义》(Moral Sentim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不可能完美:亚里士多德,女性主义和伦理学的复杂性》(The Impossibility of Perfection:Aristotle,Feminism and the Complexities of Eth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从启蒙到接受:重新思考我们的价值观(From Enlightenment to Receptivity:Rethinking our Valu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一种情感主义者的心灵理论》(A Sentimentalist Theory of Mi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人性发展与人性生活》(Human Development and Human Life,Springer,2016)。 这些著作基本反映了他的道德哲学思想发展的轨迹。 他与上述美德伦理学家共同的地方,就是强调道德哲学要更加基于人作为“行动者”的品德或美德,而反对仅仅从“行动”出发的规范或规则。 但就其美德伦理学的思想资源而言,他更倾情于苏格兰的道德情感主义,尤其是休谟的同情论,这也使得他的美德伦理更加突出地强调情感的伦理意义,由此发展出一种新的道德情感主义的美德论。 因此,与上述美德伦理学家或多或少都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不同,他的美德论很早就同亚里士多德区别开来。 哪怕1992年的《从道德到美德》宣称他“抛弃了道德概念”,同各种规范伦理学相抗争,显示美德伦理的优点,但也没有特别表现出他是支持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路向的,他只是强调:“我采取的美德伦理学将会避免使用专门的道德观念。 它的基础的德性论观念将是美德或值得赞赏的品质、行动或个人的观念。”但从2001年《出于动机的道德》开始,他的情感主义就已经形成,已经是与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完全不同的情感主义路向了。 赫斯特豪斯这样评价他是公正的:“迈克尔·斯洛特近年来提出的‘基于行动者’的美德伦理学,就不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的,而是在19世纪的伦理学家马蒂诺那里发现的美德伦理学。”在2010年的《道德情感主义》中,他终于系统地论证了美德伦理学如何必然要从行为者的内在品质和动机中去谋求善之依据和由此依据推出德行方案。 他把此称之为“基于行动者的美德伦理学”(agent⁃based virtue ethics)以区别于亚里士多德的所谓“聚焦于行动者的美德伦理学”(agent⁃focused virtue ethics),虽然这种区分在美德伦理学内部也没获得认同,但他的学说提出了两点独特的观念:人的整体优秀品质优先于行动规范:人的情感,尤其是对他人同情的共通性情感能够更好地为人的道德品质、道德动机以及道德词汇的意义提供系统的阐述。 他还进一步根据人的内在品质将他的基于行为者的情感主义美德分为三种类型:作为内在力量的道德(morality as inner strength):作为普遍仁慈的道德(morality as universal benevolence)和作为关怀的道德(morality as caring)。 这三种道德都是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的。 他的情感主义不仅仅是为一种美德寻求情感上的心理基础,更想以情感主义的方法论为整个规范伦理学建立元伦理学的基础,并进一步借助于“移情(empathy)机制”将从个体的仁慈、关怀的美德推进在法律、制度和社会习俗方面的关怀政治,从而发展出社会正义。

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
德性自我主义或尼采主义美德伦理学的代表人物是斯旺顿(Christine Swanton)。 她的代表作是《美德伦理学——一种多元论的视野》(Virtue Ethics:A Pluralistic Vie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将美德的重要特征视为“良好内在状态的表达”。 这种表述应该说非常不严格。 在一般日常语言中,它既可以是身体的良好状态,也可以是心理或生理的良好状态,究竟什么是德性的“内在良好状态”?需要更多其他的阐释和说明,甚至远不如传统的说法:一个有德性的好人,就是有好的性情或性格或有良心的人。 从他另一本著作《尼采主义的美德伦理学》中,人们当然可以发现,“内在的良好状态”,是与“精神状态”相关的,甚至更贴近地说,是与尼采的“强力意志”相关。 “道德是意志的产物”,这是西方伦理学的一个经典的和现代的命题,“意志”不仅肯定自我,而且意欲实现自我的卓越,这当然是一种美德。 但问题是,意志既可以意欲善也会意欲恶,在这种可善可恶的“自由”中,如何是“善良意志”,这是意志论道德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斯旺顿在她试图将尼采的强力意志美德化的过程中,首先想将尼采从“非道德主义”的所谓“误解”中解放出来,从美德的视角理解强力意志(Willezur Macht),这一初衷当然是新颖而且可欲的。 从她提出以“目标中心论”来评价一个行为正确性(而非美德性)而言,似乎“意志”的德性力量可以得到辩护,但是,以“目标定向”评价美德行动,似乎把“美德”和“目标”的“正当关系”颠倒了,她不是以“终极目标”来定义“善”,继而定义“美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非常明确地以人类所有活动的“终极目标”来定义“善”或“好”),而是以“美德”来定义“正确行动”。 由于这种混淆,就会直接导致“目标”被“外在化”于行动者自身的美好,当把“道德”作为去实现一种“外在目标”的“强力意志”时,也就不再是内在的美德,而将“美德”混同于一般习俗的“规范”了。 “美德”作为出于自身之美好和卓越的功夫与实践(行动),一定是内在的,其实践或行动都直接指向自身,而不以任何外在的东西为标准。 所以,在阐释“美德”时,如果脱离亚里士多德实体论的潜能—实现学说,我们就很难正确地理解何为“因其自身之故的善”和作为自身之卓越性的内在美德。 强力意志只有回到自身的美好与卓越的实现,才有可能是真正美德论的。 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立场,我们才能准确理解斯旺顿所致力于论证的“强力意志是理解尼采德性论的关键。”

克里斯廷·斯旺顿(Christine Swanton)
三、美德论者对现代规范伦理的批评靠谱吗?
表面上看,无论是康德伦理学还是功利主义这两大现代伦理学的主流,确实都以论证或阐明“行动规范”的“道德性”为主要特征,就此而言,美德论者对它们的批评似乎有理而且富有启发,传统美德在“现代”的断裂在这一问题上显然清楚地表现了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不对“现代”做个时间上的明确划分,这个批评就显得与我们所具有的哲学史知识不相符合,因为从现代开始一直到19世纪,强调德性论的哲学流派一直就未曾中断过: 英国道德哲学从萨夫茨伯里第三伯爵(Anthony Ashley Cooper,3st Earl of Shaftesbury, 1671—1713)开始就定位于德性论而非规范论,之后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 1746)作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出版《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725)、《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的阐明》(1728)和《道德哲学体系》(1755)都是在论述一种德性论的道德哲学;乃至到19世纪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高潮时期爱丁堡大学的道德哲学讲席(1764—1785)获得者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的《道德哲学要义》(Institutes of Moral Philosophy)、《圣灵学与道德哲学分析》(Analysis of Pneumaticsand Moral Philosophy)也都是情感主义德性论的。休谟(1711—1776)对美德伦理学的影响,更不用再说了,亚当·斯密(1723—1790)更是以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道德情操论》出名。
英国如此,意大利和法国同样如此,德性论从来没有被规范伦理淹没。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最著名的两部著作一是《君主论》,一是《李维史论》。被称之为“邪恶的圣经”的《君主论》虽然是向君主阐述了一套统治权术,让君主不要受任何道德法则的束缚,要内怀奸诈,外示仁慈,只需考虑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有害,对人民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但宁可与贵族为敌也不能与人民为敌。但他向君主推荐的德目依然是丰富的,我们可以说这部书是“恶德” 的传授者,但绝不能说是规范的传授者。而对于他的另一部书,现代研究者更是倾向于认为:“《李维史论》的主题,是复兴古代德行的可能性与可取性。”
在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中,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证了“论美德并非君主政府的原则”和“君主政府用什么代替美德”,阐明“美德的天然位置紧靠着自由,而并不靠近奴役,也同样地并不靠近极端的自由。”,伏尔泰(1694—1778)在他的《形而上学论》最后的“第9章”以此标题:“论美德与过恶”;爱尔维修(1715—1771)在他的《论精神》中认为认识精神就是与认识人心和感情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不得不与道德学相联系。而在“论与社会相联系的精神”这一章中,他的核心是论述“正直”的美德,论“各种保证美德的方法”,与个人、与特殊集团、与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相联系的正直。同时在 他代表作《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中有多章多节都是“论美德”。霍尔巴赫(1723— 1789)在他的《社会体系》中论述了“道德学的自然原则” “人的道德观念、意见、过恶和美德的起源”。尤其是卢梭,他延续了18世纪启蒙哲学家们主要感兴趣的思想点:“不在于使社会稳定,而在于要改变社会。他们并不追问是怎样成为它的那现状的,而是要追问怎样才能使它比那现状更好。”从这样一个思考方向上,我们就能理解卢梭为什么在伦理 学上那么重视良心、情感和德性。美国学者布拉姆甚至把他描绘成为“共和国”的“美德英雄”:“展示对‘美德’的个人热情的欲望为让 雅克·卢梭的著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他的两篇伟大演说控诉了现代社会的道德缺失;他的政治作品描绘出美德之邦的轮廓;他关于教育的小册子教导我们,一个人该如何朝着美德来提升自己;他的小说将美德 描绘成‘最甜美的感官享受’;他的自传集中描写了他‘沉醉在美德中’这一重要时刻。这些文化产品的虚构解释给让-雅克·卢梭贴上标签,认定他是一个由美德铸就的英雄。”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容易看出,美德伦理学家们对“现代规范伦理” 的批评,显然是不符合18世纪乃至19世纪前几十年的状况的。如果我们注意到安斯库姆的一个时间节点是说“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 1838—1900)及其之后的“后果主义”,那么她的批评可以接受一半。另一半,她对康德的批评,包括麦金泰尔对康德的批评,则显示出他们对康德的理解不仅表面,且不全面。麦金泰尔说:“康德提供的绝对命令的典型例子是告诉我 们不要做什么:不要背弃诺言,不要撒谎,不要自杀等。但至于我们应该从事什么活动,我 们应当追求什么目的,绝对命令却似乎保持沉默。”如果他知道康德的“绝对命令”只是 对“ 伦理义务” 之本性(obligation)——定言的约束力——的阐明,而人对自身的伦理义务和道德义务(如:作为一个道德的存在者对自身的完善性义务)本身则指明了“ 应该做” 的 目标和目的:尽其为人的本务而实现人之为人的最高道德使命,如果他同时阅读了《判断力批判》“自然目的论” 和“道德目的论” 的论证以及《道德形而上学》中的“德性论” ,他就不该得出他关于康德伦理学的那些批评了。
有意思的是,麦金泰尔对 18 世纪英国和法国伦理学史的描述,实际上与他在《追寻美德》中对“规范伦理”的批评形成了鲜明对照。他虽然从洛克的政治哲学开始讨论英国伦理思想,但列举的大多数都是我们上述提到的那些情感主义美德论思想,始终没提这些思想究竟是规范论的还是德性论的,而他最后一章的标题“现代道德哲学”显然指的是摩尔之后英美的“元伦理学” 。
总之,从道德哲学史的角度看,虽然现代人一再地感受到了传统美德在现代伦理生活中的失落、缺失、边缘化,但绝不是只有1958年之后的美德伦理学者才第一次对此提出强烈批评,实际上批评声一直不绝于耳。但是,现代之后重新呼唤传统美德或新德行,有时能够讨好,但更多的是令人怀疑和讨厌。狄德罗、休谟、卢梭都体验到了现代的道德焦虑。“狄德罗全部作品都洋溢着一种对道德的焦灼关怀” ,“一般说来,‘哲学家们’ 都像是休谟和狄德罗一样,是雄心勃勃地想要被人尊之为‘有德行的人’的。那原因恰恰在于,从他们对手的观点看来,他们乃是道德与德行的敌人”。这也就是我们上面考察的,在17—19世纪的欧洲哲学中,不断地有哲学家在构建德性论的原因。所以,也绝对不是只有1958 年之后的美德论者才开始“复兴”“美德伦理”。著名现象学家舍勒1913年就发表了一篇《德性的复苏》(Zur Rehabilitierung der Tugend),一开篇就给我们描述了这一场景: “18世纪的诗人、哲学家、教士一类的市民在呼唤德性一词时慷慨激昂,致使这个词变得 令人生厌,我们一听到或读到它,便难以忍俊。” 他更是对美德怀着崇高的敬意:“基督教的神圣象征使得德性自发地从个体的心底放出光彩,并带来这种思想:德性的善与美并不基于人对他人的行动,而是首先基于心灵本身的高贵和存在,德行对他人而言,至多不过是顺便具有意义的可见范例而已。” “现代人不再把德性理解为一种对意愿和行为的充满生机又令人欣喜的能力意识和力量意识......不仅德性的获得,而且德行本身都被当作我们的累赘。”所以,他通过对“现代人”的这种批判,从基督教而非亚里士多德复兴美德伦理:“德行根本就与一切习俗尖锐对立;德性具有内在的高贵——也只有内在的高贵才是其尺度。一般地讲,德性才能够‘使人承担义务’,才能从自身出发去规定人们可能义务的等级、品质和充足。” 这说明,在伦理学上对德性论的复兴为何一再地重新开始。
四、美德伦理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学类型吗?
这既是美德伦理学的一个内部问题,从伦理学史上看也是一个外部问题。从内部来讲,每一个当代的美德论者都试图将美德伦理作为一个完整的伦理学类型,让它作为与现代康德道义论的义务论体系和功利主义后果论相提并论的三种规范伦理之一。但实际上,无论是对于这样一种伦理体系特征的表述,还是对其规范特征的表述,都存在严重的内部分歧。正如赫斯特豪斯所言:
美德伦理学被描绘成许多样子。它被描述为:(1)一种‘以行为者为中心’而不 是‘以行为为中心’的伦理学;(2)它更关心‘是什么’,而不是‘做什么’;(3)它着手处理的是‘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我应当采取怎样的行为’;(4)它以特定的德性概念(好、优秀、美德),而不是以义务论的概念(正确、义务、责任)为基础;(5)它拒绝承认伦理学可以凭借那些能够提供具体行为指南的规则或原则的形式而法典化。
我之所以列举上述清单,是因为对美德伦理学的这些描述实在太常见,而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们很好。相反,我认为,就其粗糙的简短性而言,这些描述存在着严重的误导性。
对于任何一个完备的伦理学体系,行为者和行为,关心他能够“是什么” 和他应该“ 做什么” ,美德和义务,等等,都是不可分割的,而美德伦理学一味地为了显示自身的独特性, 强行把它们分割和对立起来,务必造成这种理论过于做作、狭隘和碎片化,其实究其根本又什么问题都不可能获得彻底的哲学阐明。因此,笔者曾经著文对此提出了强烈批评,而我的批评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分析哲学内部如弗兰克纳(William Frankena)对规范美德伦理学批评的一种延伸而已,他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给美德一个明确的、较为客观的定义,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要么成了利己主义的美德论者,要么成了功利主义美德论者,要么成了义务论的美德论者。每一种美德的定义都依赖相应的规范伦理学理论,因此,美德伦理学理论上没有自身的独立性,最多只能是其他伦理学理论的补充。”但就是这种“补充”却强行想把自己建构成独立的体系与其他理论对立起来,却又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论、知识论和价值论的基础阐明,势必给人造成了“霸王硬上弓”之感。我们只须设想一下,当代美德论者只把“美德”突出为中心以取代道德规范概念,但有的是依赖于亚里士多德,有的是依赖斯多亚主义,有的依赖休谟,有的依赖尼采,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美德”赖以成立的“哲学体系”确实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如何可能在这些相互对立的基础和主张之上形成一种美德伦理学的独立类型呢?因此,弗兰克纳的第二个批评就是:美德伦理学根本无法为我们提供正确行为的指导原则,而这却是一门伦理学应有的或主要的职责。而如果美德伦理学想要完成伦理学应有的这项职责,那么“美德依然只从属于义务和规则” 。
这才非常到位地与康德道德哲学连接上了。美德论者把康德当作批判的靶子,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德性论”作为与为行动立法的法权规范论相对的伦理学,实际上最早是 由康德正式提出来并做出了系统地论证:
伦理学在古时候意味一般伦理学说(Sittenlehre:philosophia moralis),人们也把它称之为关于义务的学说。后来人们发觉,把这个名称只用于伦理学说的一个部分是适宜的,亦即转用于单独关于义务的学说上,这些义务是不服从于外部法则的(人们在德语中恰当地给它找到德性论这个名称),于是,现在总的义务学说的体系就被划分为能够有外部法则的法权论(ius)体系和不能有外部法权的德性论(Ethica)体系。(MS:Metaphysik der Sitten,in Immanuel Kant Werke Band IV,S.5081)
康德在这里就首次把“古代” (他实际上指的是希腊化时期斯多亚主义的“古代”)作为一般规范论的“义务论”伦理体系,区分为为行动立法的外部规范(外部法则),区别于它是不能有外部法则的“德性论(Tugendlehre)”,并强调这是伦理学的“一个部分” ,这一“德性论”的“伦理学” 就是试图论证,一个有美德的人是如何确立自己行动的道德性的,这种具有“道德性”的“美德”体现为一个人的为人处事的原则上,这个原则就是行动以可普遍化的法则为自己主观的准则立法,继而把这种自律的德性法则落实为自己的义务上践行:对自身的义务,对他人的义务等。所以,不从行动的立法原理出发,“有美德的人” 如何能成为一种“规范”就是根本说不清楚的问题。
同样一直批评康德伦理学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后来明确地把一门完备的伦理学体系区分“描述的伦理学”“哲学的伦理学”和“应用的伦理学”。而“哲学的伦理学” 也称之为“ 真正的伦理学” ,以“研究人类行为的整体为对象” ,“指明历史中的 那些法则”如何使“人的本性通过理性而灵性化”(Beseelung)。任何一门伦理学都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必须包含三个各自独立的部分:“诸善论”(Güterlehre,相当于后来新康德主义提出的“价值论”)、“德性论”(Tugenglehre)和“义务论”(Pflichtslehre)。“德性论”和 “义务论”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德性和伦理存在是通过合乎义务的行为才变得能够存在” ,也就是说“每种合乎义务的行动都以德性和伦理存在为前提” ,德性和义务对于伦理学而言是相互的、对应的,体现于人的品质为德性,而德性品质必须体现为行动原则所具有的伦理性,即出于义务而尽义务的德性,所以两者不可分割,不可对立。但从分殊的角度,它们鉴于从属于“至善” 原则下可各自分述为一个体系。
从康德和施莱尔马赫丰富的哲学伦理学中,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任何试图拒绝道德、义务等规范概念的哲学根本不可能阐明“德性”,而缺失“德性论”的伦理学根本就不是“实践”伦理学,伦理学的实践必定是指向人自身“成人”,即伦理理念和道德原则内化为自身的德性品质。把两者对立起来、分割开来的伦理学显然是作茧自缚,不可能成功,因而也是没有前途的事业。因此,国内现在也有论文对美德伦理展开了批判。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美德伦理学要能在现代取得成功,真正能够成为能与义务论和后果论相提并论的伦理学体系,必须继续在实践哲学的基础理论,即实践的形而上学(伦理形而上学)上能够取得突破,并在美德伦理的相关领域进行延伸性的探究。这就是我们《伦理学术》第7期分“美德伦理学”“美德政治学”“美德法理学”和“美德认识论”等栏目深入探讨的初衷。感谢清华大学李义天教授帮我约了其中大部分稿件,感谢各位作者和译者为 美德伦理学新探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与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