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这代人再次见证了什么叫世道无常,沧海桑田。
谁也不会想到,庚子新年之交“新冠疫情”(COVID-19 Pandemic)的爆发和流行竟然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世界已经不再是那个世界,中国也不再是那个中国了;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悄无声息潜入人体的病毒会具有如此肆虐的杀伤力,把所有自鸣得意的“体制”“主义”和“高调”统统打回原形,令其狼狈不堪。汶川地震时人们带着泪水守望相助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而如今同样的天灾人祸却被各种莫名其妙的隐瞒、不负责任的“甩锅”和不明是非的争吵、蛮不讲理的谩骂和上纲上线的口水战所淹没,人情与社会的“撕裂”甚至比病毒的蔓延更为可怕地在摧毁着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人类本来就随着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工智能的崛起而被逼到了“穷途末路”,政客之间的剑拔弩张,将给人类带来一个更加充满危险和不确定的未来"。这是哲学不得不为之焦虑的当下困境。哲学想着的永远是一个问题:人类还有未来吗?这就是所谓的“存在问题”的致思方向,它的思想力量为的是催生未来之“到来”,而绝不乐意贸然宣称,根本就没有未来。
——邓安庆:《重重危机夹击下的人类还有未来吗?》(《伦理学术8——道德哲学与人类学》之“主编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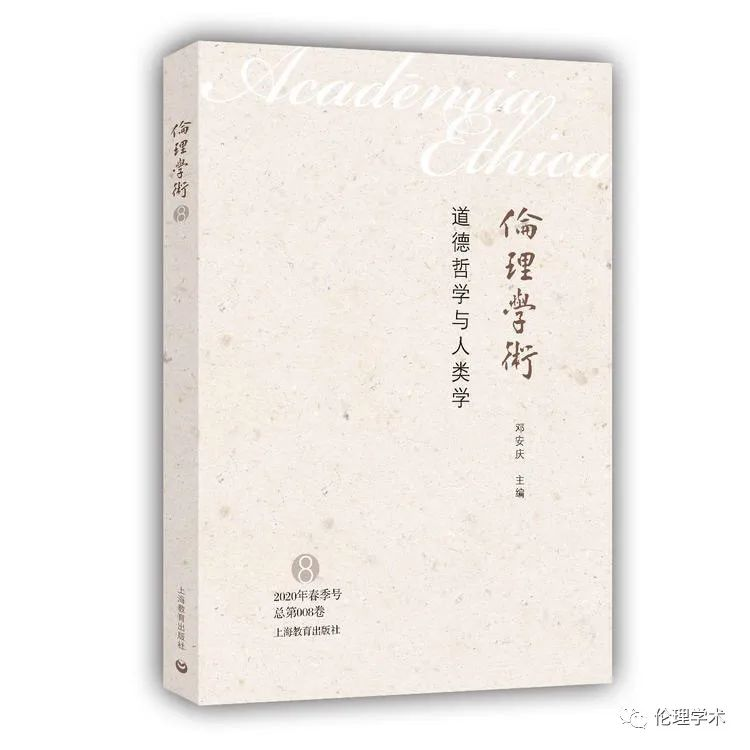
《伦理学术8——道德哲学与人类学》
2020年春季号总第008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0年6月
目录
【主编导读】
重重危机夹击下的人类还有未来吗?
邓安庆
【原典首发】
康德论医学与人的健康
——关乎哲学、自我保存与人道
「德」H. F. 克勒梅
钱康/译
Kant über Medizin und die Gesundheit des Menschen: Zum Zusammenhang von Philosophie, Selbsterhaltung und Humanität
「德」H. F. 克勒梅
论善的比较研究的前景:对人类学相对主义的阴郁主题的超越
「英」约珥·罗宾斯
马成慧/译
康德人类学的伦理维度
「美」罗伯特·B. 劳登
陈晓曦/译
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
蔡恒进 洪成晨 蔡天琪
【学术现场】
如何重建生活世界经验?
——论实存哲学的心理学意义
孙周兴
“古典美德伦理学的现代审思”研讨会精彩辩论实录(一)
邓安庆 聂敏里 张雨凝 王明磊(整理)
【规范秩序研究】
秩序伦理讲演录
陈家琪
试论黑格尔伦理学说的特质与限度
——从伦理与道德关系的角度看
庄振华
法的商谈理论与民主法治国的关键词
「德」哈贝马斯
周爱民/译 杨丽/校
【美德伦理研究】
海德格尔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
「意」佛朗哥·沃尔皮
马小虎/译 曹忠来/校
儒家耻德及其当代意义
吴龙灿
论贤者宜负重责作为德行之首的审慎
——论伯克政治思想中的德行
丁毅超
【描述伦理学】
理想·现实·外来
——《白鹿原》中的乡土伦理及其人物具象
王露璐
【书评】
哲学家身上的民族精神
——张世英《九十思问》解读
胡自信
爱这个人与爱智慧本身
——从《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看阿伦特对于爱的理解
王志宏
制度正义与秩序建立:伦理反思中的现代性生活世界
——读高兆明先生《制度伦理研究》
李金鑫
重重危机夹击下的人类还有未来吗?
邓安庆/文

“主编导读”作者:邓安庆 教授
我们这代人再次见证了什么叫世道无常,沧海桑田。
谁也不会想到,庚子新年之交“新冠疫情”(COVID-19 Pandemic)的爆发和流行竟然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世界已经不再是那个世界,中国也不再是那个中国了;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悄无声息潜入人体的病毒会具有如此肆虐的杀伤力,把所有自鸣得意的“体制”“主义”和“高调”统统打回原形,令其狼狈不堪。汶川地震时人们带着泪水守望相助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而如今同样的天灾人祸却被各种莫名其妙的隐瞒、不负责任的“甩锅”和不明是非的争吵、蛮不讲理的谩骂和上纲上线的口水战所淹没,人情与社会的“撕裂”甚至比病毒的蔓延更为可怕地在摧毁着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人类本来就随着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工智能的崛起而被逼到了“穷途末路”,政客之间的剑拔弩张,将给人类带来一个更加充满危险和不确定的未来。这是哲学不得不为之焦虑的当下困境。哲学想着的永远是一个问题:人类还有未来吗?这就是所谓的“存在问题”的致思方向,它的思想力量为的是催生未来之“到来”,而绝不乐意贸然宣称,根本就没有未来。
这当然需要基于对人性本身的深刻理解,但理解人与人性简直太难了。自从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的课题提出来之后,哲学上虽然得出了种种“人是什么”的答案,但大多数真正的智慧都止于承认苏格拉底式的“自知无知”。
对于过分相信现代工具理性的人,是不可能理解“自知无知”之智慧的。我们不会看不见,有多少人类悲剧和灾难都基于人对自身的神化和不自知。近日我们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还在讨论一位学生提交的《无知与道德责任》,她依据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些思考素材,试图为某种“无知”辩护,免去其道德责任。但在我看来,这是很难辩护成功的。对于一般个人,无知,各种无知,没有例外,必将令其承受生活中的各种打击和挫折,自己默默承受由此带来的各种责任,当然包括道德责任。对于那些能主宰他人命运的人而言,其无知,各种无知,同样没有例外,都将带来对他人和自己的各种伤害,甚至可能会带来生灵涂炭式的灾难。虽然当事人并不承认,人们在某个时刻也无法追究其什么责任,但历史是个法庭,不会放过谁的过错,不管是否故意,道德上的责任追究在人民的心中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的。当然,如果不是“无知”,而是某种意义上的“不知”,古人所言的“不知者不为错”是否适用,这确实可以探讨。
正因为对人的认识和自知如此艰难,所以对人(人性)的认识才构成了哲学永恒的难题。康德把哲学的三大主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可以期望什么,最终都归结为一个人类学问题:人是什么?他因此把伦理学区分为两个部分:伦理形而上学和道德人类学。前者为所有伦理确立其伦理性的最终标准,后者在个人的道德立法中成就有德性品质的人。因此道德哲学与人类学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是,恰恰在康德这里,人类学与哲学,包括道德哲学的关系并不总是清晰的。他一方面说,哲学总的问题可归结为人是什么的人类学问题,因而“人们可以把一切都称之为人类学”;另一方面又说,“一门纯粹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形而上学,必须把一切只是经验性的或仅仅属于人类学的东西清除干净”,这常常被认为是康德道德哲学通向形式主义的根源而遭人诟病。许多人觉得,伦理法则与道德法则如果不从经验人性中,因而不从人类学关于人的知识中确立起来,就将是无效的,它将导致伦理法则是无法落实的单纯善良意志,是空洞的形式主义等,而真正理解康德苦心的人,如伽达默尔就能断言,对康德的指摘其实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为了阐明伦理义务无条件的实践性,哲学必须脱离人的本性的一切条件性,才能超越“单纯质朴”的日常伦理理性易受蛊惑的不确定性和自相矛盾性,摆脱聪明的道德要求充满不幸的不纯粹性和功用动机之间的“令人厌恶的混杂”,在这些方面“康德具有无限的功劳”。诚然,就人类学与道德哲学的关系而言,在康德这里依然非常复杂而没有定论。
这就是本期《伦理学术》以“道德哲学与人类学”为主题的原因。
谁都会承认,道德哲学以人类善良生活和个人“成为一个人”(ein Mensch sein:是一个人)为核心,因此必须以人性为基础,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但康德为什么要把属于“人类学的东西”剔除干净,在建立起了纯粹实践的伦理法则之后再运用于人以落实于实践人类学呢?这确实有对“人类学”的不同理解在。“人类学”从其在19世纪诞生时起就属于经验科学,而不属于思辨哲学,哲学伦理学以之为基础的人类学,当然不是那种在原始部落和非洲丛林中寻找头盖骨的人类学,它也不能把伦理知识建立在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这种特殊关系中的人的知识上,当然也并非是建立在作为某个国族意义上的人的知识,即关于中国人、美国人、犹太人、德国人,如此等等,都不是一门哲学伦理学所考虑的人的知识。对于伦理学研究而言,最为可怕的一方面或者只停留在关于人性具善的或人性是恶的或人性非善非恶这样一些形而上学的假设上,而不知人性善恶或非善非恶具备哪些可能的经验性条件。就像这次新冠疫情所爆发出来的人性善良和人性丑恶,以及关于人性善良和人性丑恶的异常激烈的观念冲突,形而上学的人性假设统统失效了。另一方面,从事伦理学最为可怕的也表现在,只知道从这样一些具体经验条件下的人性知识出发,只见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而看不见人本身。人之为人的本性被淹没在家庭、出身、地位、角色这样一些特殊性东西之中了。
真正的伦理学,无论中外,都不从人的殊相论人,而是从是不是一个人的角度论人。孟子在讲善心四端、讲恻隐之心时,虽然是从一个具有思想实验性质的“孺子入井”来讲,在这一特殊情境下,你会不会救他,你救他是看“孺子”是谁家的小孩才去救的吗?显然不是,“孺子”表现的是一个“抽象的”小孩,而不是具体谁家的小孩,哪国的小孩。因而,他也就是人之为人的人,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唯有如此,孟子才能把“设想中”没有恻隐之心去救人的人称为“非人也”。其他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莫不如此,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就该有的善心,就该本着这样的善心而该做的,否则就不能算是一个“人”。孟子最后才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处的人,绝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意义上的人,而是普遍的、抽象的人。唯有在人的意义上得出的结论,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以之为基础的人类学,不是作为科学的经验人类学,而是哲学人类学。
只是,哲学人类学实际上也有理论的和实践的区分,有先验的和经验的区分。理论的哲学人类学,是从人性的各种经验表象中把握关于人的知识,在这种关于人的知识中,要确立人与非人的界限。孟子“四端说”就起着为人确立一个底线的人类学意义。亚里士多德在思考伦理学时,也是从人本性上区别于动物的兽性和神物的神性来把握人之为人的人性特征,因而在亚里士多德眼中,人是非神非兽的动物。非神,因为人的知识、智力和才能都不及神,因此神可生活在天界,对外在物质性的东西一无所需,就能过上其所意愿的永恒的极乐生活。而人的人性表现在理性能力和性情能力上,都是有限的,尤其在生存本领上,人类不能独存,在自然独存敌不过禽兽,在天独存,不具有神的神性,因而本质上人类只能作为政治动物,过城邦生活。但是城邦需要伦理才能共存,需要财富才能生活。诚然,人可以把人性发挥到完善以接近于神,譬如在思辨生活中;也可能堕落为只有兽性,如在追求财富的生活中。至于最终是神是兽,不单纯取决于天然的人性,而取决于人的美德,是否能以正义为伦理原则建立起一个好的城邦制度。好的城邦制度能激发和造就人的美德,人的美德也完全可能被坏的城邦制度所毁坏而变得禽兽不如。因而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政治学基于自然人性的伦理化。城邦与人在自然人性从潜能到实现的自由造化基础上相互生成与完善。这实际上也就过渡到人的德性自由造化的实践人类学上了。有意思的是,亚里士多德是要把在柏拉图那里作为至高存在的善的理念限定于“属人的善”(Gut für Mensch),而康德在伦理形而上学中却彻底清除了仅仅属于经验性的和人类学的东西,之后才把普遍有效的伦理法则落实于“实践的人类学”(die praktische Anthropologie),才得以最终回答人是什么这一最终的或全部的哲学问题。所谓实践的人类学,在康德这里最核心的要义,就是通过“实践立法”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本质,通过实践立法,人将自己的行动设立在实现成为一个自由存在者的自我造就的道路上。我们生而为人只是一个自然人,一个自然人如果不能自我造化为一个自由存在者,那就很容易失去人性,甚至可能成为一个禽兽不如的动物。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道德的使命,把自己塑造成为真正的德性人格。
在此意义上,法权哲学为行动立法,实现人作为一个具有外在自由的法权意义上的人,法权意义上的法是解决行动的正当性,其标准在于你的自由任性和他人的自由任性能在一个普遍法则之下相互一致而共存。法权意义上的正当性,是伦理关系正义性的保证,体现在尊重他人与自己一样的自由及其权利,这种权利的实现只要是基于普遍法则,那么我的自由任性和你的自由任性就能相生而不相害。基于法权的正当性的行为者就会将自身塑造成为一个具有伦理正义的社会人格。
德性哲学为个人的行为准则立法,要解决行为的道德性,以确立自我的内在自由,其标准是自我立法的主观准则能同所有有理性存在者的意志法则相一致。因此,德性法则的道德性将把不要求道德动机的法权义务变成自觉自愿践行的德性义务,以此实现人的自我完善的自由德性。于是,康德的实践人类学分别从法权人格和德性人格,即伦理人格和道德人格实现了人作为一个自由存在者的道德使命。完成了人的道德使命,一个人才真正地自我造就为一个人了。这就如同哲学人类学家盖伦(Arnold Gehlen)所言:“人出自本性地是一个文化存在者(der Mensch von Natur ein Kulturwesen ist)。”实践人类学最终会成为文化人类学。
为了真正展现康德人类学的伦理与道德之维度,本期特别约请了当代两位著名康德专家和一位人类学专家专门为我们撰写文章,在我们这里首发,他们是:《康德研究》主编克勒梅教授,专门撰写了《康德论医学与人的健康》;美国著名康德专家罗伯特·B. 劳登(Robert B. Louden),专门撰写了《康德人类学的伦理维度》;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西格丽德·罗辛(Sigrid Rausing)头衔教授、剑桥马普伦理经济社会变革研究中心主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约珥·罗宾斯(Joel Robbins),撰写了《论善的比较研究的前景:对人类学相对主义的阴郁主题的超越》。这三位中的两位,即克勒梅和罗宾斯,是我们《伦理学术》的学术委员。此三文论,各有侧重,相得益彰。
《康德论医学与人的健康》论述了康德一生都致力于掌握当时前沿的医学专业知识,使自己具备必要能力审查其医学科学提出的有效性或真实性诉求,以厘清哲学与医学对于人的健康,对于人作为一个自由存在者的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关系。显然,医学不只是治疗身体的疾病,同时也医治精神的疾病。康德虽然是个二元论者,但他相信身体和心灵相互影响、互为健康的条件。当一个人被剥夺了研究和教育的自由,受损害的不仅他们的思想,同时也有其身体,如大脑。所以,在让事物之本性变得完善的道路上,医生与哲学家之间不会有什么矛盾。哲学的精神不仅能消极地预防疾病,而且能积极地以养生学的方式成就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他还以想象力的自由活动讨论了疑心病和眩晕的治疗方法。康德以其独特的哲学养生术让自己在那个困难的时代获得健康与高寿,其特别推荐的方法有自由散步、审美想象力的自由游戏、愉快的社交聚餐等,这些都与自我保存与人道相关。
《康德人类学的伦理维度》指出,人类学是在启蒙时代成为大学里的一门学科的,康德的人类学是伦理人类学,属于“实用人类学”的子集,它通过提供与人类相关的经验知识以揭示伦理之根源,从而有助于伦理进步。虽然学术界对于康德人类学思想的定位存在分歧,但无论如何只把人类学解读为纯粹道德哲学的补充是难以成立的。康德完全能够相信,人性的经验知识可以运用于道德目的,促进伦理共同体的发展与完善。人类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其理性部分可以促进道德,其受制于情感的倾向则阻碍着道德。因此,澄清康德伦理人类学可以健全关于伦理的世界知识,有助于道德教育与品格发展,进而促成人类最终过上和平而有道德的生活。
《论善的比较研究的前景:对人类学相对主义的阴郁主题的超越》则是对1980年之后西方人类学主题变换的思考。谢里·奥特纳于2016年发表了一篇题为《阴郁的人类学与它的理论对手:八十年代以来的理论》的文章,指出当代人类学研究已经转向了对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具体而言,就是专注于“新自由主义”政治纲领实施以来所产生的社会不平等、贫困和社群衰败等问题,作者称这种人类学研究为“阴郁的人类学”。同时,奥特纳与之不同地提出了,我们需要确立一种对于善观念进行批评反思的人类学,来对抗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负面效应。罗宾斯不同意奥特纳对人类学走向的这种判断,因为人类学对新自由主义秩序阴暗面的研究并非刚刚起步,而以对抗新自由主义为目标的善的人类学也未必能够很好地实现奥特纳设定的理论任务。所以,他通过与奥特纳的对话,主要想达成两个理论目标:其一,善观念批评考察的人类学应该以价值多元主义为基础,考察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善观念,应该超越奥特纳将人类学研究仅仅限制在抗争新自由主义阴暗面这一狭窄的思路,让人类学具有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其二,揭示人类学在当代影响力式微的原因,在于人类学自身视野的局限,这种局限实际上来自经验的局限。要克服这一局限,单纯依赖人类学自身是无法做到的。实践哲学的处境意识和由此走向治疗性的实践人类学依然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人类到了21世纪,科学技术达到了日新月异的高度,但人类确实已经病得不轻。有的是纯然的现代病,有的却依然是古墓僵尸病。为此,本期特发孙周兴教授《如何重建生活世界经验?——论实存哲学的心理学意义》这篇在第六届中国精神分析大会上的长篇演讲和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卓尔智联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和人工智能研究的科学家蔡恒进教授的《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这两篇大作与前3篇关于人类学的文章相比,更为直接地探讨人类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困扰全球的生态危机、政治危机和技术统治的异化现实下,文化似乎已经病入膏肓,人类还有未来吗?如果相信人类有未来,医治人类文化疾病的“哲学心理学”将从何处寻求生命的健全力量,生命意志?还是人工智能?不管它们究竟是拯救的力量还是摧毁的力量,人类要能生存下去,如何学会与自然和睦相处、如何与自身的本能欲望和理性欲望和睦相处以及如何与AI机器人和睦相处,已经是每个人必须思考的迫切问题了。
在我们的经典栏目“规范秩序研究”下发表了陈家琪教授的《秩序伦理讲演录》、庄振华教授的《试论黑格尔伦理学说的特质与限度》和哈贝马斯的《法的商谈理论与民主法治国的关键词》。陈家琪教授借助于约翰.塞尔在《社会实在的建构》一书中对“无情性事实”(Brute facts)与“制度性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的区分,讨论群体生活的伦理秩序,把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区分开来,但这两种秩序又都归结为“制度性事实”以区别于“无情性事实”,但“无情性事实”究竟是哪些事实呢?他试图在中国历史上寻找这两种事实的表现形态,以理解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以及政治秩序所具有的伦理意味。
庄振华教授的论文重提关于道德性与伦理性两种实践哲学传统之争,认为黑格尔虽然反对康德道德主观主义,但其伦理思想始终还是以康德道德哲学为参照系,甚至将之当作现代普遍的世界观。黑格尔本人并不拒绝道德,但主张使道德扎根于“事情本身”之中,这事情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伦理性。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关注风俗伦常的思想家不乏其人,维科、伏尔泰和赫尔德对各民族风俗的比较更使这方面的研究蔚然成风,但是,像黑格尔这样将生活的伦理性发展成一个庞大体系,并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历史这些通常被认为与伦理有所差异的东西纳入一个逻辑条贯的伦理学架构中的,却再无第二人。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黑格尔伦理思想内在的局限,正如谢林批判的那样,他过度强调事物观念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事物原初发生,即原初伦理关系在存在论上的呈现,他在批判和超越现代主观性哲学的同时也与其他现代思想一道预设了一种内在性的世界观,遗忘了伦理形态先于理性的崇高秩序。
哈贝马斯作为当代规范秩序研究的领袖人物,我们在思考现代规范秩序重建的时候,他的思想绝不能够缺席。在《法的商谈理论与民主法治国的关键词》中,哈贝马斯阐明了他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这本堪称现代规范秩序经典著作中选择商谈理论方法的四个动机。首要的一个,就是在功能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恪守传统的民主理念不再可能,交往理论才能兼顾复杂的现代性与传统民主;传统的自然法和现代实证法之分歧也需要依赖一种商谈伦理的程序原则;“人民主权”和“法律的统治”这一现代法治主义的内在困境,自由主义法律范式和社会国家法律范式之间的冲突,都需要商谈伦理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理念和方法。
在另一个经典栏目“美德伦理研究”中我们刊登了三篇大作。
一是意大利著名海德格尔研究专家,长期探究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之关系的佛朗哥·沃尔皮的《海德格尔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该文指出,尽管海德格尔本人忽视了实践哲学,在明显给予存在论以优先地位的时候拒斥通常的伦理学,但是,他在20年代的研讨班上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虽然他的工作重点是去伦理化,将伦理问题存在论化,但是这一工作却启发了他的学生们,在20世纪最令人绝望的时刻,开启了当代实践哲学的复兴之路。海德格尔的学生们没有全盘接受他存在论化。而是在实践哲学的框架下复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阿伦特对实践(praxis)的重建,伽达默尔对实践智慧(phronesis)的重建,里特尔对伦理(ethos)的重建都为当代伦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吴龙灿教授的《儒家耻德及其当代意义》。该文认为先秦儒家已经洞悉耻在伦理生活中的根源性地位,羞耻感既是人禽之别的底线,也是道德行为的动力。在西方关于羞耻观念的参照下,我们可以发现,耻即为孟子的道德本心或四端之心。从道德角度看,“耻”对于确立道德自我,树立道德理想,培育道德仁心,努力成就君子人格,都是基础性的价值。从伦理角度看,“耻”作为仁心在人伦关系的不同范围中扩充为忠恕之道、礼乐教化和正义原则。“耻”是人摆脱动物性走向人性、超越人性走向神圣性的价值理性,是善恶之辩的枢机。重视耻德具有普遍意义。
其三,国内对于作为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一直缺乏深入研究,尤其是其政治伦理,连介绍的都非常少。为此,本期专门约请丁毅超博士撰写了这篇《作为德行之首的审慎——论伯克政治思想中的德行》,希望以此推动关于保守主义的政治伦理的探究。
与此相应,为了把当今国内外许多精彩的学术会议讨论的内容尽快反映出来,我们在本卷开始,专辟了一个“学术现场”栏目,本期刊登的是我们今年元月初新冠疫情已经爆发而毫不知情的特殊情况下参加的“古典美德伦理学的现代审思”会议的精彩辩论实录(上),力图留下学术交锋时的思想火花。
在《描述伦理学》栏目下刊登了致力于“乡村伦理”重建的王露璐教授的《理想·现实·外来——<白鹿原>中的“乡土伦理”及其人物具象》。
在我们特别看重的“书评”栏目,刊登了胡自信教授为今年百岁高寿的张世英先生《九十思问》的解读文章:《哲学家身上的民族精神》;王志宏教授的《爱这个人与爱智慧本身——从<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看阿伦特对于爱的理解》和李金鑫博士撰写的《制度正义与秩序建立:伦理反思中的现代性生活世界》,通过解读高兆明《制度伦理研究》,以寄托我们对于他不幸离世的哀思。
编完本期文稿,越发感觉到做道德哲学的不易。正如尼古拉哈特曼所言,“伦理学是人心中首要的、最实际的哲学兴趣……是哲学思维的起源和最内在的动机,……而且亦是哲学思维与一般人类思维的终极目标和最大展望。伦理学活于未来中,它永远将目光朝向远方的东西和非现实的东西,甚至要求以未来的视角看待当前的东西,因为它是超时间的”。可是同时,伦理学的问题意识又无不来源于现实的处境,来源于对经验人性的观察与反思。可是,就是这个经验的人性太过于丰富和复杂了,它有时纯洁得像天使,崇高得像神灵,令人敬仰,而有时又堕落得禽兽不如,表现得如同一只疯狗,令人厌恶。我们既期望“天不变道亦不变”地把握人间“常道”,尽情至性地享受静好时光,欣赏荷塘月色,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总是伴随着人类的日常。伦理学不仅需要高度的形而上的思辨,同时又必须阐明面临各种复杂处境的“实践智慧”。虽然“明智”(pronesis)起来对于人而言永远不会太晚,但是伦理的实践智慧绝非能够靠背记书本知识和标准答案而来,它是从做人为人的伦理生活中而来。过于聪明的人常常只知“权变”而不知遵守常道法则的重要,而过于本分的人却又只懂常道而不知权变,最终失去对人之为人最为重要的自由之价值的领悟。
在我们共同经历这场世纪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有“闲潭云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的哀叹,但同时不要完全失去对人性的信心,对神性的敬仰,对未来的思索。人类真的是到了最为危险的时刻,人类究竟有没有未来,最终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明白该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