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术12——伦理自然主义与规范伦理学》

邓安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伦理学术》丛刊主编。
我们的儒学研究者一直不太重视莱布尼茨—沃尔夫关于儒家伦理思想的研究,尤其没有对儒家伦理哲学对欧洲启蒙运动在观念上和信念上的建设性影响做深入研究,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如果我们至今依然热衷于只把儒家哲学视为我们先人阐发的一套关于中国古人安身立命的学问,一种仅仅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知识”,而看不到也不重视儒家哲学曾经有过的世界历史意义,认识不了它在17-18世纪参与欧洲现代转型中所起到的激进引导作用,我们自己也就会失去让儒学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和视野,会因我们自己的眼界而把儒家狭隘地归于一种“保守主义”,从而蒙蔽和贬低了儒家本有的世界关怀所体现出的普遍大道和崇高伦理精神。
无论是莱布尼茨还是沃尔夫,他们不是狭隘而偏私地依据自己的个人喜好而赞美儒家,而是以他们所把握的数学工具发现与建构儒家经典中存在的普遍的“道德语法”,从而把儒学放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来理解和把握;他们也远远不是仅仅考察一个秉持儒家伦理的理性人如何道义地行动的原理,而是探究在儒家的“自然理性”基础上如何按照数学的方法发展出一套“普遍实践哲学”。这恰恰是我们当代学者不得不具备的哲学视野与功夫。
......
——邓安庆《儒家伦理与伦理自然主义问题》(《伦理学术12——伦理自然主义与规范伦理学》之“主编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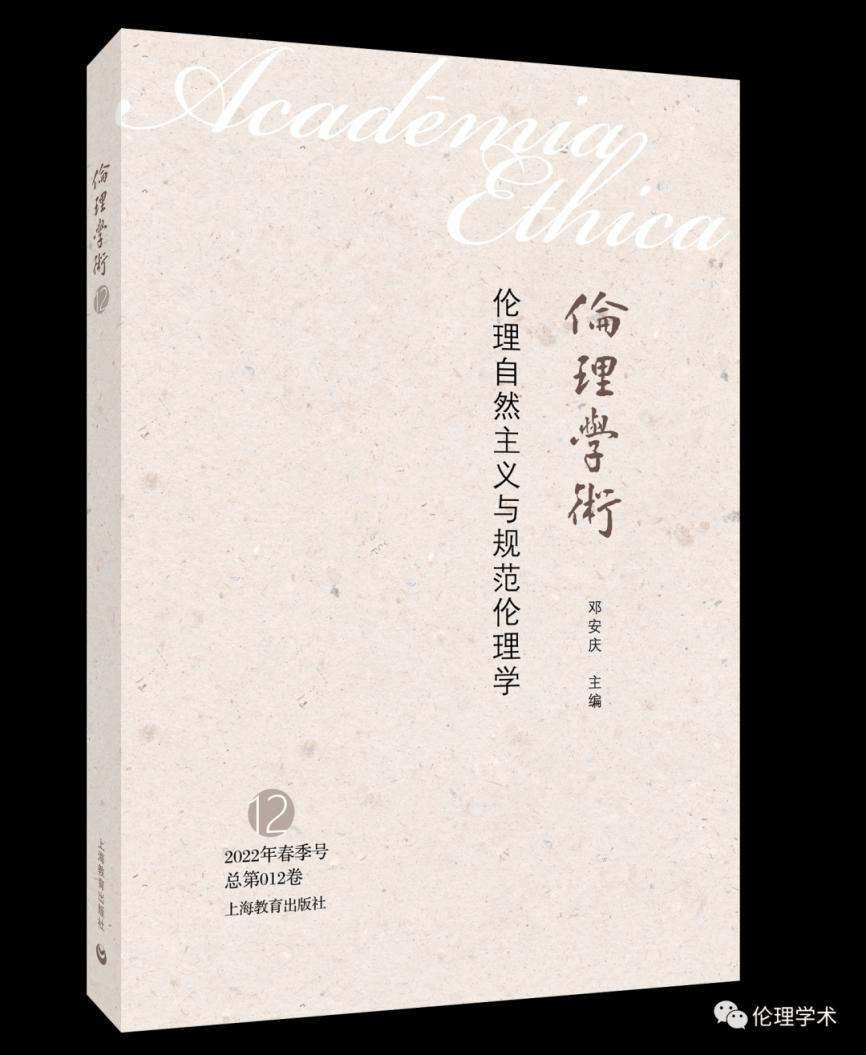
《伦理学术12——伦理自然主义与规范伦理学》
2022年春季号总第012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2年8月
目 录
【主编导读】
01 儒家伦理与伦理自然主义问题
邓安庆
【原典首发】
09 “道德不要主人”——论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对儒家伦理学的解释
「德」罗哲海 钱 康/译
34 康德论普遍意志:定言命令之功能的对等物?
「德」克里斯托夫·霍恩 贺 腾 王博韬/译
【霍布斯道德哲学研究】
49 霍布斯的道德观
「英」霍华德·沃伦德 陈江进/译
63 霍布斯与心理利己主义
「美」伯纳德·格特 高 雪 毛兴贵/译
81 霍布斯与伦理自然主义
「美」琼·汉普顿 曹 钦/译
103 霍布斯的道德哲学
「美」汤姆·索雷尔 文 雅/译
124 霍布斯自然法的明智解释与道德解释之辩
王 博
【康德伦理学研究】
137 康德的人类学理念
「德」诺伯特·欣斯克 陈联营/译
149 康德的魔鬼民族及其国家
「德」米夏埃尔·帕夫利克 黄钰洲/译
171 康德“学院—世界”的哲学概念:世界公民智慧的启蒙
张 广
181 《判断力批判》与柏拉图伦理学
钟 锦
191 康德意念思想发微
马 彪
【规范秩序研究】
205 再论伊拉斯谟与马丁·路德关于自由意志的辩论
黄 丁
219 普遍意志的两次建构:论“耶拿精神哲学”中的社会与国家
蒋 益
【书评】
238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汉学视野中的墨家伦理学书写
刘 松 邹天雨
254 布伦塔诺:伦理的自然约束和情感明察
曾 云
266 电影《阴谋》中的道德、法与政治
陈家琪
儒家伦理与伦理自然主义问题
邓安庆/著

▲ “主编导读”作者:邓安庆 教授
2021年7月12日,对于研究儒家道德哲学的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为了纪念时任哈勒大学副校长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用拉丁文发表《中国人的实践哲学演讲》300周年,德国哈勒大学“启蒙运动哲学—沃尔夫学会”、哈勒大学哲学研讨班/国际康德论坛、“欧洲启蒙运动跨学科研究中心”以及哈勒沃尔夫故居/城市博物馆联合举办了纪念活动。之所以如此隆重地纪念300年前关于中国儒学伦理的一个讲话,原因不言自明,我们依然生活在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现代性之中。而在启蒙运动轰轰烈烈进行之时,儒家伦理哲学在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学派的话语谱系中,作为依赖“自然理性”而无须依赖宗教(无论是自然宗教还是启示宗教)就能建构起和谐有序、文明知礼、富裕繁荣的东方文化典范,欧洲人对此充满了好奇与想象,因而儒家伦理在西方起到了反对基督教神学统治、弘扬自然的世俗理性的“激进启蒙”的作用。当然,沃尔夫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演讲不仅冒犯了他的继任者、神学家朗格(Joachim Lange),而且激怒了整个大学神学系乃至普鲁士国王威廉"腓特烈一世,引火烧身,使得“启蒙理性”与“正统神学”的尖锐斗争具体化为沃尔夫主张的儒家自然理性与虔敬派神学信念之间的斗争,结果真是像“火星落入了火药之中那样立刻爆发出愤怒的火焰”,“激起了民众、宫廷,乃至整个德国对沃尔夫先生的愤怒”。国王无法忍受沃尔夫所谓“自然理性”之“邪说”,动用他手中的至上“威权”,于1723年11月8日下令沃尔夫必须在48小时内滚出普鲁士王国,否则上绞刑架处死。沃尔夫“秀才遇到兵”,连夜仓皇出逃,在黑森—卡塞尔公爵的庇护下任教于马堡大学。
我们的儒学研究者一直不太重视莱布尼茨—沃尔夫关于儒家伦理思想的研究,尤其没有对儒家伦理哲学对欧洲启蒙运动在观念上和信念上的建设性影响做深入研究,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如果我们至今依然热衷于只把儒家哲学视为我们先人阐发的一套关于中国古人安身立命的学问,一种仅仅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知识”,而看不到也不重视儒家哲学曾经有过的世界历史意义,认识不了它在17-18世纪参与欧洲现代转型中所起到的激进引导作用,我们自己也就会失去让儒学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和视野,会因我们自己的眼界而把儒家狭隘地归于一种“保守主义”,从而蒙蔽和贬低了儒家本有的世界关怀所体现出的普遍大道和崇高伦理精神。无论是莱布尼茨还是沃尔夫,他们不是狭隘而偏私地依据自己的个人喜好而赞美儒家,而是以他们所把握的数学工具发现与建构儒家经典中存在的普遍的“道德语法”,从而把儒学放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来理解和把握;他们也远远不是仅仅考察一个秉持儒家伦理的理性人如何道义地行动的原理,而是探究在儒家的“自然理性”基础上如何按照数学的方法发展出一套“普遍实践哲学”。这恰恰是我们当代学者不得不具备的哲学视野与功夫。
我们《伦理学术》密切关注了哈勒大学举办的这次盛会,我们也凭借这次盛会的学术负责人克勒梅(H.F. Klemme)教授和重要的主旨报告人、著名汉学家罗哲海(Heiner Roetz)教授担任《伦理学术》“学术委员”之便,让他们把会议论文交给我们“首发”,并得到了他们的欣然同意。我们在上一期发表了克勒梅教授的主旨报告《依赖与治权:笛卡尔与康德之间的沃尔夫〈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1721年)》,我们在这一期继续发表罗哲海教授在会议之后专门为我们精心修改过的主旨报告:《“道德不要主人”——论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对儒家伦理学的解释》。前者通过比较笛卡尔的“临时性道德”与沃尔夫通过儒家自然理性证成的普遍实践哲学,阐明“无信仰的”中国人的实践哲学具有和有信仰的普鲁士人的实践哲学同样的“自由和无畏”,把理性的自由法则视为源自自然法,儒家道德哲学发现:
理性人的行动出自对善的洞见,非理性人的行动则出自“对主人的畏惧”。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确信:理性是“自由之理由”,独立与自治权是自由之本质特征;这一点虽由他——沃尔夫,才第一次被明确表达出来,但早已被古代中国人预见到。“若一个人行善乃是出自对善的明确知识,避恶乃出自对恶的明确知识,那么他的行善避恶就出自完全的自由。”
国内许多为儒学辩护的学者至今也秉持一种意见,说如果儒学基于自由就不是儒学了。但只要我们承认儒学是一种道德哲学,那么说道德不基于自由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沃尔夫恰恰就是把他心目中崇高的儒家实践哲学建构在“自由”的基础上。他赞美儒学的理由,既不是认为儒家有一套道德形而上学,也不认为儒家有一套清晰的概念系统,相反,他恰恰认为,儒家依赖于对善的直觉性知识而可通达“自由”。关于善的直觉,对儒家而言,确实是最为根本的,儒家先哲不认为概念上清晰是思想的美德,反而总是让弟子们在生命体悟中去切身地感受模糊不清的概念之含义,直觉地把握概念蕴含的自然天道,从而知道“善恶”是如何运行的。真正的自由,对儒家而言,不是意志的任意选择,而是对天道(自然法则)的“顺从”。
这也就是罗哲海教授《“道德不要主人”——论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对儒家伦理学的解释》的基本思路,他清晰地认识到,“对沃尔夫来说,中国是一个用来证明自然的‘内在动因’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力量能够走得多远之试验的例证”。这是用自然理性去体悟自然法则(天道)的伦理自然主义进路。在沃尔夫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宗教的框架虽然作为“背景”而保留了下来,“伦理善”从而具有了绝对命令性的形式,但同时在实践上成为“多余的”东西,因为中国的“榜样”使他明确地看到,善的秩序并非来自上帝的命令,“自然机制本身就足以‘实践美德并避免罪恶’”,理性自由的自律足以担保善的律法:“因为我们通过理性知道自然法则的意志;因此一个有理性的人不需要其他的法律,而是仅仅通过他的理性本身,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法律。”
于是,我们通过这两篇探讨沃尔夫的儒家道德哲学阐释的论文,深刻感受到伦理自然主义和伦理建构主义之间的张力,在解决当今全球伦理失范中的意义与限度。正是受此触动,本期《伦理学术》聚焦“伦理自然主义与规范伦理学”,以两个专栏为核心。一个是由西南大学毛兴贵教授主持的“霍布斯道德哲学研究”专栏,刊登了英国霍华德·沃伦德的《霍布斯的道德观》(陈江进译),汤姆·索雷尔的《霍布斯的道德哲学》(文雅译);美国伯纳德·格特的《霍布斯与心理利己主义》(高雪、毛兴贵译),琼·汉普顿的《霍布斯与伦理自然主义》(曹钦译);以及王博的《霍布斯自然法的明智解释与道德解释之辩》五篇文章。
在道德哲学史上,正如毛兴贵教授所言,霍布斯在何种意义上具有道德哲学,他的道德哲学论证采取“何种进路”,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我们伦理学界都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本专栏所发表的这四篇翻译论文是国际知名专家们精深研究的最新成果,霍华德·沃伦德认为,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要解释“国家”这个庞大政治强权的合法性来源,无论这个强权有多邪恶,只要它具有统治的效力,那么必然在某种意义上是得到了公民“自愿服从”的某种“信约”的,这种解释因其反抗了一般民众心理而具有强大刺激性。因为对国家强权表达服从,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亲身体会,出于“恐惧”,出于“怕死”,或出于某种聪明的利益算计,这是一般弱民们“服从”的心理基础,但要说服从政治强权的统治,是得到了我们自愿同意的“信约”,则大多数不能认可。但霍布斯恰恰试图让人相信:“被征服者之所以有义务服从,不是因为被更强的力量征服了,而是因为他已经通过信约表达了服从。”这一步跨越为他的论证增加了困难。霍华德·沃伦德试图证明,霍布斯恰恰是通过阐明,公民“基本盘”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产生了“他们应该服从主权者”这一“信约”,政治权力就获得了其“统治”的有效性,因而在探讨如何“应该”服从政治权威的意义上,霍布斯就可以被视为一位“道德主义者”。他的整个政治哲学虽然拒绝了自由意志的基础,强调的是基于理性算计后的“同意”与“信约”,也拒绝考虑同意背后的“动机”,但他最终依据的是自然法解释。他使自然法的解释具有了形式化的特征,最少化的自然法条目都源自对人的自然本性的经验假设。在此意义上,把霍布斯的道德哲学进路视为“自然主义”就是合理的,也是其自然法极具创新之所在。
这也就让人们不能不把霍布斯的道德哲学与“心理的利己主义”算计联系起来。伯纳德·格特在其《霍布斯与心理利己主义》中明确反对了霍华德·沃伦德对霍布斯道德哲学做心理利己主义的解释,他说,“心理利己主义”在哲学上的吸引力就在于,它主张人们从不会为了利他而行动,或者因为相信某种行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而行动。但是,心理利己主义的“成功”,必须满足于哲学上的普遍性论证要求,仅仅说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行为由自利动机驱动,并没有提出任何哲学问题,真正在哲学上令人感兴趣的是要证明,所有人的所有行为完全都是由自利驱动的。心理利己主义或利己主义人性观在道德哲学上的正确性,取决于对全称判断的利己动机的科学证明。伯纳德·格特要证明的却是,他并不否认霍布斯持有一种悲观的利己的人性观,但他否认霍布斯秉持的就是一种利己主义心理学,相反,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心理利己主义并不相容。这种“辩证”对于我们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无论人们是否承认上述两篇文章中的具体观点,他们似乎都同意,霍布斯的道德哲学进路是“自然主义”的。琼·汉普顿的《霍布斯与伦理自然主义》对这一自然主义进路作了非常清晰而合理的阐明。霍布斯建构了“道德科学”这一概念,把“道德哲学的科学”(a science of moral philosophy)视为同伽利略、开普勒和哈维所推进的物理科学并驾齐驱的“科学理论”,这使得霍布斯的道德哲学秉持鲜明的伦理自然主义的进路而不断被人所追随。但琼·汉普顿这篇文章新颖地试图证明,霍布斯“伦理自然主义”进路的“表面合理性”绝非因为把一切事实最终还原为可经验的“物理事实”这一“物理主义”,而恰恰取决于把自己宣称要绕开的“形而上学无稽之谈”悄悄地吸收了进来。因此,这篇文章的意义也不能从文章标题的表面含义来解读,它不是简单地为霍布斯的道德哲学提供一种伦理自然主义的辩护,相反,它试图阐明,伦理自然主义进路本身具有很强的误导性。与霍布斯有着同样的“形而上学顾虑”的当代道德理论家,他们也都与霍布斯一样,在如下问题上被误导了:在何种程度上,伦理自然主义能够避免把它认为不恰当的形而上学“无稽之谈”偷偷地吸收进来?所以他宣称,这篇论文不是反对伦理自然主义本身,而仅仅是反对这种进路的霍布斯版本,因为恰恰是霍布斯的进路所具有的问题,严重到足以使任何伦理自然主义者担忧的地步。
有意思的是,汤姆·索雷尔的《霍布斯的道德哲学》避免了霍布斯阐释中伦理自然主义与隐蔽的形而上学之间的矛盾,直接从“美德论”来阐释。而这种美德论也不是当今美德伦理学的那种进路,它没有宣称以美德为元概念,也不是以一个有美德的人出发论美德。相反,霍布斯是遵从自然法的“行动”来定义美德:“按照这些和其他有助于我们保存的自然法行动的习惯,我们称之为美德;而与之相反的习惯,则称之为恶品。比如,正义就是我们遵守信约的习惯,相反的,不正义就是恶品;公道就是我们承认天性平等的习惯,傲慢则是恶品;感恩就是我们借以得到他人好处和信任的习惯,忘恩负义则是恶品;节制是使我们戒除一切会导致我们毁灭的事物的习惯,无节制则是恶品;明智和一般的美德是一样的。”可见,霍布斯的道德哲学即包含了义务论的内容,也包含了美德论的内容,它们都可以从伦理自然主义获得支持,但伦理自然主义必须找到某种处理形而上学问题的框架,否则伦理的自然性和伦理的绝对道义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获得充分阐释的。
由此我们可见,如同一般“自然主义”一直含义不清一样,“伦理自然主义”同样很难让人清晰地知道其含义的边界。某人的思想如果被人指称为“自然主义”,一般是指这种思想或者是从“自然性”或“自然的事实”出发解释所有的现象,它将一切与“自然”相对的“人为的”“价值的”和“精神的”现象也一同纳入“自然的东西”来解释,即把所有现象最终都还原为“自然的基础”;或者仅仅秉持自然主义的方法论,认为人类在寻求自然知识的过程中,除了依靠自然科学提供方法论之外,根本不存在任何别的可靠的方法论能对自然的、伦理的、历史的、精神的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前一种“自然主义”也被称之为“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是“强自然主义”,认为世界上除了“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实体”之外,不存在任何非自然的与超自然的实体;后一种被称之为“方法论的自然主义”,是相对较弱版本的自然主义,后来在分析哲学中进一步被“弱化”为一种“研究进路”,而不必是一种方法论理论。
由于早期探讨宇宙本原的哲学家同时都是科学家,“科学”就在“哲学”中,因而对世界本原的解释,实际上就是对世界“科学的”解释,在此意义上,哲学与“自然主义”同根同源。但自从苏格拉底创立了“伦理学”之后,伦理知识的核心是人类的存在机制,人类共存相生的德性知识,这些知识源自“认识你自己”的人性,是“属人之善”。显然“人性”不是“自然的物性”,人性也要从“自然出发”加以解释,因为“人的自然”即“人的本性”,“本性”即“自然”。但是,毕竟人的“本性”不是“自然造化”就可完成的,它是一个未完成时,需要在人类社会、伦理、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自我造化来完成,所以伦理之知,不可能完全从“自然”来解释,德性也不能全然是“自然主义”的。总之,随着“伦理学”的出现,也就出现了一种不同于物理之知的伦理和德性之知,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这一点非常明确地被我们认识到了。
到了亚里士多德,人类知识才从整体上被分类。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典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许多“科学”的创始者。在他那里,“哲学”依然就是“科学”,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事物“原因”的解释。但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出现了被20世纪的自然主义所反对的“第一哲学”观念,“哲学”被他规定为关于所有事物“第一因”的研究,因而在“理论知识”或“理论哲学”中就有一门“科学”是研究“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学问,它不探究时间、空间中的“自然事物”“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使之成为该事物,而是探究“是”之为“是”的学问。“第一哲学”于是作为最高的“思辨科学”成为哲学的代名词,具有了对于所有“科学”的优势地位。而这是20世纪的“自然主义”所极力反对的。
但在20世纪“自然主义”尚未兴起之前,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一直被视为区分“哲学思维”与“科学思维”的门槛,古代哲学或多或少都具有某种“自然主义进路”,但自从休谟提出从“事实”(自然的东西)推导不出“价值”以后,“强自然主义”就遭受到“危机”。伦理学上,英国哲学家、伦理学家G.E.摩尔在其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中,首次提出“自然主义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伦理学”之划分,“伦理自然主义”就与“伦理形而上学”对峙了起来:
自然主义伦理学的“效力”(Geltung)归功于这一假定:能够被定义为“善的”是同一种“自然的对象”相关联的。我认为这种理论以这一章的标题所使用的表达,称之为“自然主义的伦理学”(Naturalistische Ethik)。需要注意的是,我为定义“形而上学伦理学”(Metaphysichen Ethik)引出了那个错误推理,按类型说是同样的,我给予这种错误推理一个唯一的名称,叫“自然主义的谬误”(Naturalistischer Fehlschluβ)。
但这种区分本身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被称之为“自然主义的伦理学”的可能同时也是包含“形而上学”论证的,譬如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它的整个论证的基础是“自然主义的目的论”,而自然主义目的论的成功论证又是与他的“是其所是”从“潜能到实现”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摩尔批评“形而上学伦理学”犯下“自然主义谬误”之后,20世纪伦理学在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短暂地“拒斥形而上学”之后,在20世纪上半叶,对杜威的实用主义伦理学,R.W.塞拉斯、拉蒙特等人的自然主义伦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蒯因(W. V. Quine)1968年在题为“自然化的认识论”的公开演讲之后,分析哲学内部发生了所谓的“自然主义转向”或“自然主义革命”,伦理自然主义成为一个被视为没有“自然主义谬误”的伦理学进路得到许多人的高度认同,尤其是摩尔开辟的语言分析的元伦理学或者走向直觉主义,或者走向情感主义,难以解决现实生活中重大的伦理困境,而生物学、遗传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反倒让人们对伦理问题有了重大的认识上的推进,这更促成了伦理自然主义的复兴。
但是,无论自然科学在“说明”世界时具有多么重要的特权,也无法掩盖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伦理现象不可能“还原”为“物理事实”而得到透彻的解释,因为人生、人性乃至人类的伦理生活不可能源自“物理事实”而只能源自“理性事实”。因此,我们从康德伦理学中就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继承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从斯多亚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三分的知识结构,但另一方面他完全避开了休谟发现的从“自然”推导不出“价值”的困难,重建了“道德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在超越休谟的过程中他发现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不是从“自然”推导出“价值”,而是如何从“价值”变成“有效规范”,即那些不可认识,却具有先天立法功能的超验的本体价值(自由、灵魂和上帝)如何具有立法的规范有效性问题。所以,他才通过将传统逻辑学改造为“先验逻辑”,以“先验论证”解决“应该做什么”的自由基础和道德性标准,伦理法则的规范有效性和绝对命令性的特点由此得到合乎自然的阐明。伦理学变成了与物理学探讨自然因果性相对的、探讨自由因果性的“道德哲学”,才对人如何成为一个人,如何活出人本该具有的尊严和正义的自由生活,做出了最为经典的理论阐明。因此,在康德这里,伦理自然主义被改造成为伦理的理性建构主义,是不再具有“自然主义谬误”而同时又不再依赖于超自然实体来阐释伦理价值与规范的自然正当性基础。
所以,本期《伦理学术》另一个核心是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除了德国波恩大学著名哲学家克里斯托夫·霍恩为本刊撰写的《康德论普遍意志:定言命令之功能的对等物?》之外,我们还刊发了德国特里尔大学的诺伯特·欣斯克的《康德的人类学理念》,德国弗赖堡大学米夏埃尔·帕夫利克的《康德的魔鬼民族及其国家》,以及国内学者张广的《康德“学院—世界”的哲学概念:世界公民智慧的启蒙》、钟锦的《〈判断力批判〉与柏拉图伦理学》和马彪的《康德意念思想发微》,这些文章都给我们提供了对康德伦理思想的新的阐释。
同时本期还有五篇非常值得重视的文章,黄丁的《再论伊拉斯谟与马丁·路德关于自由意志的辩论》将我们带到了宗教改革时代伊拉斯谟与马丁·路德关于意志是否自由的长期争论之中;曾云的《布伦塔诺:伦理的自然约束和情感明察》也非常切题地将现象学伦理学的奠基人布伦塔诺的伦理思想展示在我们面前;蒋益的《普遍意志的两次建构:论“耶拿精神哲学”中的社会与国家》探讨了黑格尔耶拿时期精神哲学的伦理基础建构;刘松、邹天雨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汉学视野中的墨家伦理学书写》介绍了我们并不重视的西方汉学家对墨家伦理学的研究;尤其要提到的是陈家琪教授对德国电影《阴谋》中艾希曼等纳粹分子关于对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会议的道德、法与政治的哲学解读。作为《伦理学术》的主编,我非常感谢所有作者和译者给中国伦理学术提供了一场思想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