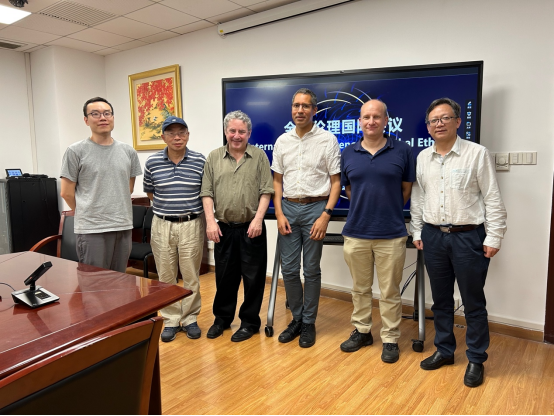2023年9月21日,复旦大学全球伦理中心建设与发展座谈会于复旦大学顺利召开。复旦大学全球伦理中心委员会成员与海外学者一同参与座谈,与会者有复旦大学全球伦理中心主任邓安庆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伦理中心副主任王金林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伦理中心秘书长钱康青年副研究员,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Jon Mandle教授,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经济、伦理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人类学系主任Joel Robbins 教授以及伦敦大学学院公共卫生伦理专家James Wilson教授。

会议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向国外学界介绍复旦大学全球伦理中心(后文简称“中心”)的建立初衷与未来规划。第二,了解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学者对重建全球伦理的看法与中心后续发展的期待。第三,拟定中心与国际学界的初步合作方式与方向,邀请更多国际学者加入中心,共同参与中心建设、一同谋划中心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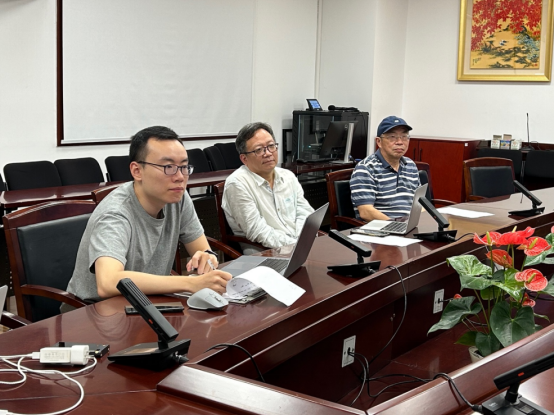
邓安庆教授简述了中心的创设初衷与初步规划。中心于2022年成立,那时正值疫情,各国都处于封闭之中,国际交流受阻,国际矛盾激化。灾难提醒我们新的国际形势已然形成,国际规范秩序的重建迫在眉睫。哲学必须担此重担,建构新的全球意识、重启全球伦理的探讨。在此背景之下,中心意图在新的自由的国际秩序中引领各国传统伦理转向,反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这一任务要求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因此,中心一方面邀请各位教授担任中心的学术委员、研究成员;另一方面定期开展会议,增进国际学术交流。
王金林教授提出了中心的两个任务。第一,构建“一个全球伦理”(a global ethic),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前提下探索全球伦理的普遍原则与普世价值;第二,建设“全球性的伦理学”(global ethics),关注全球性的问题,引导世界范围的、跨国界的学术合作,开展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的研究工作。
钱康秘书长对即将举行的“第一届全球伦理国际会议”做出说明,指出本次论坛核心宗旨在于探索全球伦理的可能性。首先,“全球”界定了伦理问题的讨论视角,虽然多元文化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哲学必须致力于考察普遍有效的伦理原则,将之与地方性或民族性的具体的伦理生活区分开来;其次,论坛的目的在于探索全球伦理原则的规范性基础,而非提出一系列价值主张。确立特殊价值背后的普世价值固然重要,但这并非论坛的意图,也不是哲学的任务。
随后,国外学者基于各自的学术背景,就全球伦理重建的可能性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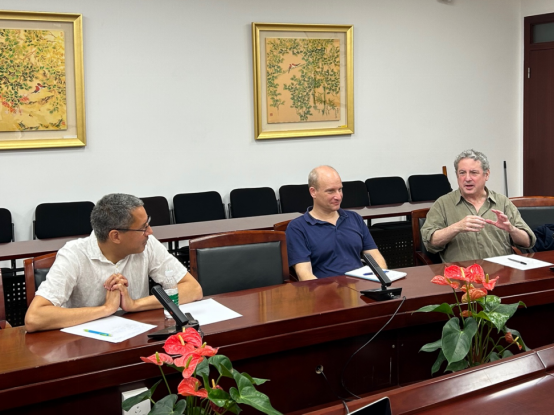
Wilson教授致力于医疗和健康与哲学的交叉领域,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共医疗中的人权问题、公共医疗系统的建立及其发展。他强调即便我们是在哲学层面上讨论伦理,但也不能忽视实际生活中时刻发生着的伦理困境。
Mandle教授指出全球伦理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如何在承认多样性的同时保留共识。他认为罗尔斯的理论为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路径。在《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中,罗尔斯处理的正是国际和全球范围内的多样性与共享习俗之间的张力,并要求在包容彼此差异的价值观的前提下,建立共享的价值系统。
Robbins教授分享了人类学研究如何有助于思考文化多样性。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当地的基督教化导致了传统观念与基督教观念之间的冲突,而这种价值观的更迭与冲突也恰是我们当下的处境。此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类学家对于价值的关注愈发强烈,并试图在哲学中寻找思想资源,但是现有的讨论并不令人满意。同时,哲学式的价值讨论也使得人类学家对多元文化的兴趣减弱,他们从考察现存的文化与习俗转而关心什么是我们必须或说应当共享的,并试图以后者干预前者。而Robbins教授本人的兴趣依然是人类学式的,即从世界上现存的诸多道德规范与价值观念出发,思考多样性所扮演的角色。

Wilson教授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将确立普遍的伦理原则与达成全球共识视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必要条件,那么全球伦理的实现便值得怀疑。其原因有二:首先,某个文化传统内部也难以达成共识,享有相近的伦理价值的群体内部依然存在冲突;其次,即便有普遍的伦理原则,也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比如传染病造成的影响中的不平等,或是气候变化和经济危机。有限资源与分配不公导致的不平等似乎是比普遍原则的缺失更为棘手的问题。
钱康秘书长对Wilson的质疑做出如下回应。首先,中心的首要任务并非全球伦理的实现,而是探索全球伦理的可能性,因为全球伦理当被视为一个范导性的理念。其次,全球伦理并不需要直接处理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因为理论与实际的伦理困境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距离,但只有确保我们在相同的基础上讨论价值,我们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与处理才有客观的立足点。不过,Wilson教授的看法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它说明哲学有其自身的使命与限度。至于普遍伦理原则的探索,我们可以以人权为例。人权被作为基础性的东西,这说明了人们已经开始探索适用于不同文化的普遍价值。在西方的语境中,人权大多被等同于自由与尊严,在中国的宪法中也是如此,这说明我们对人权的价值具有相近的看法。所以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普遍价值的缺失,而在于我们对人权的内涵做出了不同的阐释,而这要求我们从人权的抽象概念出发,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人具有诸多基本权利。
Mandle教授就人权与全球伦理的可能性进行了补充。一方面,罗尔斯将人权视为合法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的要求,并将自由权作为首要的人权。虽然这个观点经常被批评为对权利的狭隘化,但对罗尔斯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界定权利的目的是建立最小的合法秩序,而非对人类整体的命运进行规定。尊重人权的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在这个基础上,个人才能追求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罗尔斯将他的理论视为对于实在的乌托邦(realistic utopia)的建构,其乌托邦性质显而易见,因为理论只能提出“事情应当如何”的规范性要求;但他依然试图将理想的政治秩序与现存世界联系起来,因为在他看来正义的社会以及由理想调整的世界秩序是可能的,并且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有价值,它至少能令我们克服绝望。此外,就Wilson教授谈到的共识无法可能的问题,如果仅仅寻求共识,那么很多可怕的共识被共享与支持,而哲学思考的目的恰恰在于避免这种结果的产生,因为我们所做的并非引导人们达成某个特定的共识,而是寻求达成共识的合理方式,以使共识具有理性的基础。
Robbins教授指出了对于多样性的包容是共识的内在要求。通常被视为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其实并不能免于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的价值预设,因此,比如人类学家若要考察印第安人的文化,就要摆脱西方社会科学的视角而成为一名印第安的社会学家。因此,全球伦理首先需要理解多元文化,而非对其进行价值判断或排序,并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如何形成不同文化的共同语言,进而谈论共识。

最后,邓安庆教授指出中心作为全球伦理的国际交流枢纽的重要作用。中心目前与德国学界的联系较多,包括法兰克福规范秩序研究中心、柏林自由大学全球正义研究中心、哈勒的跨学科启蒙运动研究中心。因而,复旦大学全球伦理中心一方面可以作为英语学界与德语学界交流的渠道;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中国与国际学界合作的桥梁。国际学术交流可以以任何方式展开,比如开展线上与线下讲座、讨论会;不但面向学者而且面向学生,使整个学界获得伦理的全球性视野。此外,中心还可承担外文著作的翻译与出版工作,使优秀的研究跨越国界与语言的隔阂,帮助优秀的学者扩大国际影响。
座谈会顺利结束,与会成员合影留念。